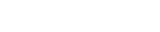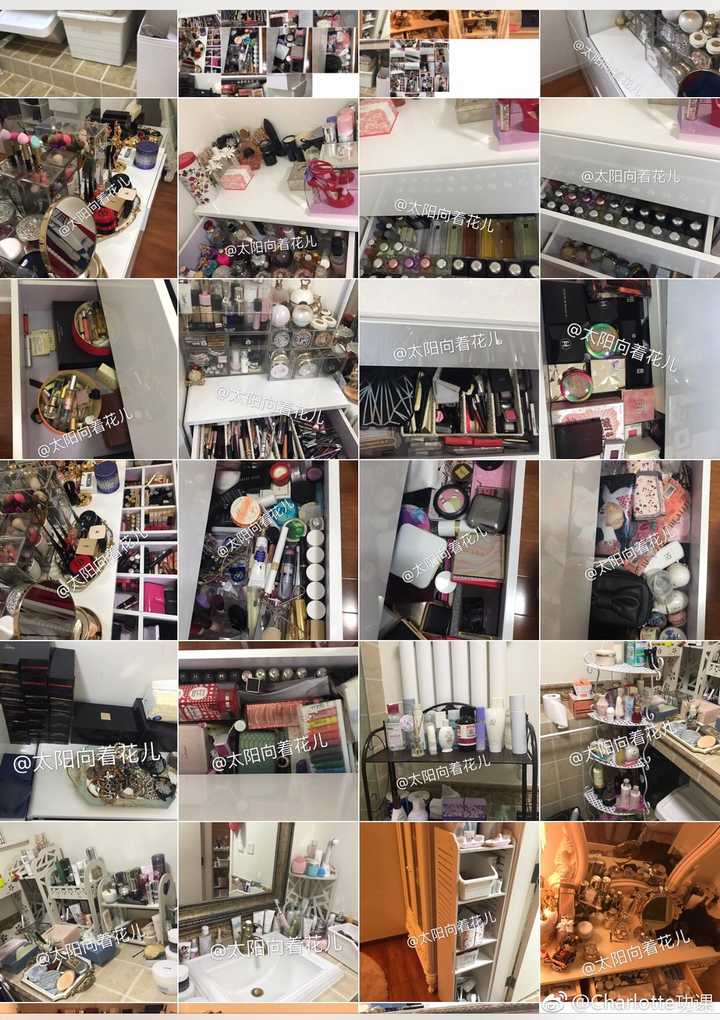文章插图
徐翠萍 摄
1.
【 阮文生|石头、泥沙、清水和来回 | 老头】这里我来过,又不像来过。我把自己怀疑上了。我有点呆了。主要是五座牌坊,竖在面前,前所未有。我僵直着,被石头卡住,目光也僵直了。我不能顺利地看鼻子底下的萝卜青菜,更多温暖的样子,都在阳光里。不像早晨,黄山冬天的早雾就像冰箱里的水气,我被狠狠地冷冻了一回。我在骑车,手和车龙头一样又冷又硬。天气一阵阵的,不好说。山脊线在波动,由于贴在牌坊的后面,我还是能看到一大团色彩,主要是绿的,也有灰的,还有一些我说不上来的意味。我一点点地看,一座座地看。这样能弄清一些来龙去脉。
这地方叫葵姑,是岭下苏村水口处,往大一点说,是安徽黄山区永丰乡。
1965年,五座牌坊被打碎。因为和水库扯到一块,我把它想成冬天的活动,那年头冬闲修水库是普遍的。沿山水库的基坝涵洞需要石块,就用打碎的牌坊去补洞吧!冬天搬动石块,手吃不消的。早晨我扶着车把,虽然戴着手套,一上午也没暖和过来。有人和我握手,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?也可能是夏天发生的事。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想法,没有热量催发不出的。
1965年,这些累加的石块,足够一些地方沉重又冰冷,也足够一些嗓音红涨着脸,而不远处的兴修水利是火热的。这样的连接和设想,应该是破天荒的。这么说下去,铁锤对准牌坊不可避免。肌肉在空中大块鼓突,动作在平台抡得又圆又狠。“轰”的一声,牌坊倒下,一团响亮一团粉尘同时从泥土里腾起。足够多的脚再踏上去。石块运到水里反复清洗。一个设想一个工程差不多了。后来,一波又一波的涟漪,在水鸟的羽毛下日见稳定日益丰满。
我在发呆。似乎发足了呆,才能清醒过来。这时没有风,中午的阳光是大团大团的温暖,我的背脊有点汗水蠢动,仿佛是对曾经的冷冻的补偿。1965年,我够不着。1990年代,葵姑已被撕开一个大缺口,除了空白还是空白。现在我把自己怀疑上了,因为空白面目皆非了。其实是牵动了我的来来回回。
那一回,我和一个朋友骑自行车从县城往这里来。乡下中学的文友已经给我买好了市面少见的花生。离葵姑不远的公路上布满沙子。一个老农从头到脚地披着稻草出现了,下坡的路面让一些情况变得古怪、突然又猛烈。应该说,那时候我有些冲。车子撞上了老头。我们一起倒地。真是要命!我用带血的双手扶起老头。他大声地呻吟,让我六神无主。郊游的心情一点没有了。没想到村里的书记是一个学生家长。老头是他的村民也是他的长辈。他用我不懂的土话和老头说话。又让我去小卖部买些东西来。等我从目的地回来时看情况再说。
同行的朋友是陪我的,顺带他去乡下看看女同学。单身少女的房间里,少见的蓝格子红方块床单。纸鸽子要飞不飞的样子,是床横头里的一个动态。床头柜、一排书、台灯、铁皮饼干盒被格式化。淡淡的清香似有若无。乡下的墙壁不够白,可女同学的脸白里透红,她压轴般地坐床上和凳子上的我们交谈着。总之,信用社的几平方米的房间里的安宁温馨,被压缩也深化了。
中学里的文友,在单身房间里摆开招待的架式。几张骨牌凳围住火锅和酒,至今温暖又清晰。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,是横着来的,让椅子凳子接住脚。大家一起说着酒话。同行的朋友惦记着女同学,她已经名花有主,但不防碍他在这个夜晚不断地喊着她的名字。可我却被撞人的事弄得心绪破碎。一经酒水,伤疼火辣辣起来。我晓得,一个年老的生命,离死是近的,这么一撞,离死更近了。要是一晚过来,老头死了怎办啊?
还好,一切都过来了。一个段落是艰难的,即使落下血疤。总的来说,时间是通畅的,暴殄、苦痛和忧思堵不住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,五座牌坊仿佛一队生灵,从大雾里消失,又从原野里突围了。葵姑还是葵姑,坦平的土地里是萝卜青菜,侧面的山脊还在不停地起伏。
2014年冬修水利,村民们发现了水库里的石块,像发现新大陆,激动和不安让苏村沸腾了,一个决定就像当年的炮声,从水库冲天而起。捞上来捞上来,花多大代价也得捞上来。真是糟糕!脾气火暴的后生骂起来!应该是孙子在骂爷爷。他们激烈地争辩着谁是真正的罪人。2014年,2015年,苏村异常繁忙。几乎全村人出动了,铁器和石块碰得震天响,丢进水里的东西又回来了,沉甸甸的担子在肩头晃悠。满是泥巴和伤痕的石头,在葵姑摆开架势,就像回到久远里的那场准备。2016年,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努力下,每块石头就像断裂的骨骼,对准原来的位置和高度重接。很好,没一点错位。破碎的记忆开始完整。那些榫头再次清晰!一切重新开始,它们整齐划一,阅兵式的步伐一般,走过岁月和原野。